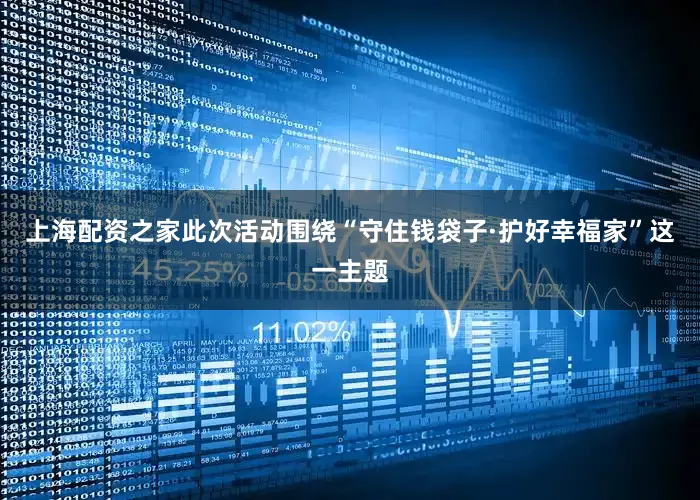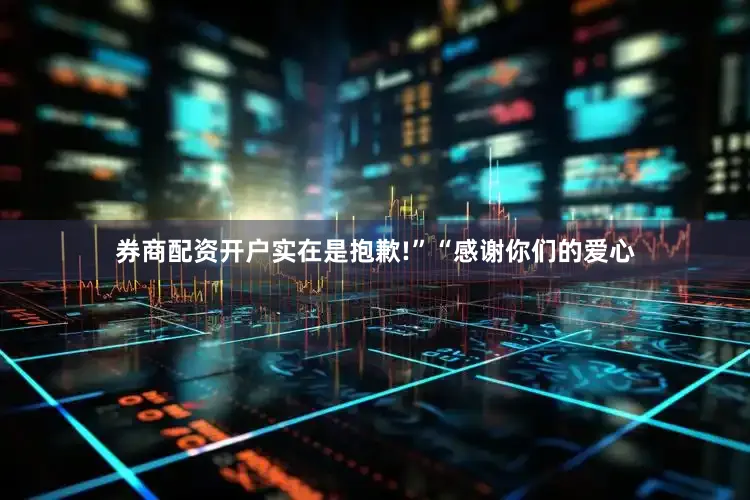图片
——此篇字数六千有余,静性以学,与君共勉!
欢迎来到 Book-Book-精品馆
“君子之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 刘开谋篇第十
“谋”,即谋略、谋划,指施展谋略计策。
《谋篇》是游说谋略的扩展,是《权篇》的姊妹篇。
《权篇》更加注重于对形势的判断,更多地停留在分析阶段。
《谋篇》则侧重于实事求是,提倡一种务实的态度。
《鬼谷子》认为,“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指出 “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 的本质,强调因人制宜,“因事而裁之”的游说方略,以及 “天地造化,在高与深;圣人之制道,在隐与匿” 的行事法则。
《谋篇》,句式一
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审得其情,乃立三仪。三仪者:曰上,曰中,曰下,参以立焉,以生奇。 奇不知其所雍,始于古之所从。故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
【译文】
凡是筹划计谋都要遵循一定的规律,首先要追寻所面临问题的起因,进而探求事物发展过程特别是现在的各种情况。 掌握了这些情况,才可继而制定三种计策。所谓三种策略,就是上策、中策、下策,把它们互相参验,就能够定出良策奇谋。真正的良策奇谋是无所阻挡、无往而不胜的,这种设计奇谋的方法是古人就曽实施过的。所以郑国人入山采玉时, 都要带上指南车,就是为了不迷失方向。考察他人的才干,衡量他人的能力,揣度他人的真情,就好像是做事时使用指南车一样。
【拆解】
“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
任何谋略的制定都有其内在规律,核心在于先找到事物的根源、依据,再探究其真实状况与本质。
“道” 在此指谋划的客观规律,如同治水需顺水性、耕田需合农时,谋略的 “道” 也需贴合事物的本质。
不循道,则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纵有奇思妙想,也只是空中楼阁。
古之谋士如郭嘉、荀彧为君主献策前,必先穷尽 “所因” 与 “所情”,非此则难成大计。
“必得其所因” 之 “因”,是事物发展的源头。
“得因” ,即找到这些源头的依据,医者诊病只有先查是什么样的病因,才能对症下药。
“以求其情” 之 “情”,是事物的实际状态与本质。
“求情” 是在 “得因” 基础上的进一步探究,如同剥茧抽丝,逐层揭开表象,触及核心。
曹操与袁绍官渡之战前,荀彧 “四胜四败” 论正是 “求情” :不被袁绍 “兵多将广” 的表象所迷惑,反而察其 “内部不和、谋而不决” 的真实之 “情” 状,坚定了曹操与其决战的信心。
“情” 的复杂性在于经常被掩盖,故所 “求” 之需通过反复排查、多方求证,避免被 “伪情” 所误导,这是使得谋略的实施能够符合现实情况的关键。
“得其所因” 与 “以求其情” ,二者在谋略的实施过程中缺一不可,唯有使他们结合运用,才能让谋略真正的 “对症下药”。
若只 “得因” 而不 “求情”,则易执着于既往经验、规律而忽视实际状况;若只 “求情” 而不 “得因”,则易流于表面,而不知其内在的规律。
商鞅变法,既 “得” 秦国 “积弱” 之因,又 “求” 秦国 “民欲强” 之情,故其法既能破旧,又能立新规,终成强秦之策。
“凡谋有道” 的 “道”,便是不凭主观臆断,不依书本教条,而是遵循 “因” 与 “情” 的客观事实。
历史上,许多失败的谋略皆因背离此 “道”。
宋襄公泓水之战,固守 “君子不重伤”而无视 “战场以胜为要” 的实 “情”,终致惨败;
马谡守街亭,照搬 “居高临下” 的兵法,却不 “求” 其战略布局 “无水” 的实 “情”,终致失守。
可见,“道” ,不在于运用一些花里胡哨的技巧,而在于遵守客观规律,认清现实,承认事物的发展有其自身逻辑,谋略需顺应这种逻辑,而非强行扭曲。
任何高明的谋划,都始于对 “因” 的探寻和对 “情” 的洞察,而非凭空的灵感或玄妙的算计。
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在解决某些较为困难的问题前,你是否有先问自己这些 “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思考的每一步,每一个细节都要罗列出来,认真仔细的了解这件事情的困难的地方在于什么?办法有什么?解决的过程是怎么样的?解决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解决办法有没有漏洞?这个困难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是外因还是内因?是外因的话,能否通过某些渠道解决?是内因,自身能否克服这些?解决过后会不会对后续某些事情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会不会侵害某些人的利益?解决过程产生的代价自己能否承受?不解决的话这件事情会产生哪些隐患?等等,通过多方面充分考量,反复揣摩,即可把握问题的关键、难点。
当完完全全能够把握问题的关键之时,所谓解决问题也就不再是所谓解决,而是顺应问题当下的实际情况,根据外界与自身所处在的客观规律使问题在发展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自我消解,而非扩大。
这种 “得因求情” 的思维,让谋略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成为每个人可践行的方法 —— 从客观实际出发,而非主观臆断,这正是 “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 这句话的精妙之处。
“审得其情,乃立三仪
这一句强调在透彻掌握事物真实状况后,方可确立上、中、下三种策略。
“审得” ,即经过验证的、全面的了解。
唯有如此,“三仪” 的设立才不会是空想,而是基于实际的推演。
三仪者:曰上,曰中,曰下
“三仪者:曰上,曰中,曰下”,即是明确三种策略的层级划分,各有其适用场景与目标。
“上仪” 是理想状态下的最优解 —— 需天时、地利、人和俱备,收益最大且风险最小;
“中仪” 是常规状态下的稳妥解 —— 只拥有部分能成事的条件,收益与风险持平;
“下仪” 是危机状态下的保底解 —— 只有在应对最坏情况下才能使用,虽收益甚微,却能达到最低风险。
“上仪” 的核心是 “取势”—— 借大势之力达成目标,无需过多消耗自身资源。
它依赖于 “情” ,不仅要知 “可为”,更要知 “何时可为”“如何借势为”。
如商鞅变法,是借秦孝公 “急于强国” 的决心、百姓 “渴望改变” 的心态,以及六国 “相互攻伐” 的外部环境,顺势推出新法,故能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
“上仪” 的难点在于 “势” 的不可控性 —— 若大势突变,最优解可能会直接失效,故需以 “中仪” “下仪” 对策,有备无患。
“中仪” 的难点在于 “稳健”—— 不冒过大风险,在合理范围内达成目标。
它是 “审情” 之后对现实条件的妥协,不可奢望 “上仪” 的完美,也不会沦入为下之策。
蔺相如 “完璧归赵” ,亦如中仪之策:若秦王真心换璧,便是上仪,则可顺利完成赵国使命;若秦王诈璧,便是下仪,则以 “碎璧” 相胁保全国体。
这种策略不求 “必得”,但求 “不失”,对多数谋划而言,“中仪” 是最常采用的选择,因其兼顾较好的可行性与有效性,能在复杂多变的 “情” 中保持定力。
“下仪” 的本质是 “保底”—— 为最坏结果预设防线,确保核心利益不受损。
这一对策的使用,能够即便使所有有利条件消失、不利因素产生了较大的危害,也能留有退路。
刘邦被项羽困于荥阳时,陈平献 “金蝉脱壳” 之计:让纪信假扮刘邦诈降,刘邦则趁乱突围,虽损失纪信与部分兵力,却保住了刘邦的性命。
“下仪” 之策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它能够为 “上仪”“中仪” 之策托底,避免因一次失策而满盘皆输。
参以立焉,以生奇
“参以立焉” 之 “参”,是根据实际变化让三者相互参照、补充。
“立焉” 强调最终策略的形成需融合三仪:可能以 “上仪” 为目标,完成之后便以 “中仪” 保全自身、瞒天过海,以 “下仪” 为退路之法,金蝉脱壳;
也可能根据局势变化,从 “上仪” 退守 “中仪”,或从 “中仪” 升级 “上仪”。
因此, “参” 不是随意使上中下仪相互叠加,而是为了让策略始终符合实际情况,与事物的发展规律互相同步。
“三仪” 更偏向于 “稳妥” 的策略,而“生奇”则有可能会是直接 “破局” 的关键,二者缺一不可。
不懂 “立三仪” 而求 “奇” 者,如马谡 “舍水上山”,无任何退路,虽是奇则奇矣,然终致惨败;
只知 “三仪” 而不能 “生奇” 者,如赵括 “照搬兵法”,虽有上中下策,却无可应变之法,终被秦军围歼。
“奇不知其所雍,始于古之所从”
“奇策” 的特质便是在于让人“不知其所雍”。
而“奇” 之策所以难以被破解,正因它打破了常规的思维。
但 “奇” 并非是突然灵光一闪亦或是毫无章法的策略。
如 “围魏救赵” :魏军本以为攻打赵国之后,援助赵国的齐军会直接支援赵国,却不料齐军乘魏国兵力空虚之际直击魏国都城,这一 “奇” 策让魏国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回救则前功尽弃,不救则都城危急。
“奇不知其所雍” 之 “雍”,指阻塞、抵御。
“不知其所雍”,源于它跳出了对手预设的思想框架。
常规策略有迹可循,如攻城必用云梯,对手可预设滚石来进行防御,而奇策则如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或用对手意想不到的手段,亦或攻击对手意想不到的薄弱点。
这种 “无迹” 会让对手的防御手段直接失去作用,如同用盾牌抵挡弓箭,谁知四面八方全是箭雨,防不是办法,不防更不是办法,不知其所防,更不知如何防之,只用盾牌作为防御手段的对手自然也就 “不知其所雍”了。
然而,“奇” 的这种 “潜规则” 往往被常规思维所忽略,如同太阳东升西落便是人人可见的显规则,而地球自转人人虽知但不可见是潜规则。
不可听,不可见,不可嗅,奇策的特质正在于可潜而行之,用之,而不可为人所察觉,由此才能在显规则的框架外找到突破口,让对手的常规手段失效。
“始于古之所从” 的 “古之所从”,指自古以来被验证的根本规律,如因果规律、人性规律、事理发展规律。
奇策之 “奇” 是形式上的新颖,而非本质上的荒诞 —— 它的内核始终贴合 “古之所从”。
如诸葛亮能够做到 “草船借箭”,形式上是 “借敌之箭” 的奇思,本质上却是遵循 “大雾会阻挡人的视线” 的自然规律与 “曹操生性多疑而不敢出战” 的人性规律。
这便是 “古之所从” ,它如同大地,而奇策便是如同生长在大地的奇花异草,然而,无论其形态再怎么奇特,也离不开土壤的滋养。
尚若脱离 “古之所从” 之 “奇”,便是无源之水。
亦如永动机,看似新奇却无法实现,因为它背离的自然法则,背离了自然发展的规律,世间的万事万物皆不可能永久存在,何况是一部机器。
“始于古之所从” 之 “始”,便是强调奇策的创新来源于对古老规律的应用,而非背离。
古人云 “道法自然”,“古之所从” 便是经过时间沉淀之 “道”,奇策则是 “道” 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表现。
孙武曰 “兵者,诡道也” 也是 “古之所从”,而韩信 “背水一战”、岳飞 “连结河朔” 都可以是源于这一 “道” 的奇策。
这种 “始” 不是复制、复刻,而是运用古老的规律,并加以修饰,使其契合当下的实际情况,让奇策既符合规律,又能因地制宜的使用。
若只知 “古之所从” 而不加以修正,使其符合现实情况,便会沦为教条主义;
若只求新奇而背离 “古之所从”,导致其成为脱离实际的空想、幻想之策,则会沦为妄谈。
“故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
这一句以郑人采玉的典故揭示行事需有恒定指引的道理。
玉石多藏于深山险谷,路径崎岖难辨,郑人携带司南车,是借其恒定指向锚定方向 —— 无论山林迷雾遮眼、岔路丛生,司南始终是不偏移的坐标,让采玉者在复杂环境中不会迷失。
这里的 “司南之车”,是 “原则” 与 “方向” 的隐喻:人在追求目标时,若没有类似司南的恒定指引,便易被外界干扰,如诱惑、困难、流言所带偏,最终导致 “惑而不得”。
“载司南之车” 之 “载”,强调正确且长期的 “指引” 。
郑人并非偶尔使用司南,而是将其 “载” 于车中,视作采玉的必备前提:宁可多花些力气和时间携带确定准确方向的工具,也不冒风险。
这种 “载” 的态度,恰是成事的关键,如同航海者离不开罗盘、旅人离不开地图,人在复杂事务中,必须主动确立并坚守核心原则,并将其视为行动的 “司南”。
商鞅变法时,“信赏必罚” 便是他的 “司南”,无论旧贵族阻挠、百姓质疑,始终 “载之而行”,终让新法深入人心。
“为其不惑也” 的 “不惑”,是 “有司南” ,便可在变数之中保持方向。
采玉途中或许要翻越高山,绕开悬崖,但司南的存在让郑人清楚 “虽绕路,目标恒在”;
同理,人在成事过程中也难免会遇挫,但有 “司南” 在,便不会因任何挫折怀疑自己的方向,也不会因岔路迷失初心。
孔子周游列国 “累累若丧家之犬”,却始终坚守 “克己复礼” 之 “司南”,终成 一代孔圣。
郑人取玉的 “玉” 是目标,“司南” 是达成目标的准确方向;人生之 “玉” 可以是理想、成就、功德,而“司南” 便是支撑其实现的信念。
无 “司南” 者,若是没有恒定的方向,便不知从何处着手,达到何处的目标,随遇而安,虽然偶得小利,终会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中迷失自我;
而有 “司南” 者,纵使路途曲折,也能在自我的坚守之中步步靠近目标。
古往今来,凡成大事者,皆如郑人载司南,以恒定原则对抗世事之变幻,终得 “不惑” 之境,因其心中有 “司南”,则行有所向,惑有所解,事有所成也。
“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
这一段则是将 “度材、量能、揣情” 三者比作行事的 “司南之车”,强调其对事的指引作用。
“度材” 是衡量他人的材质,如能力、品性、特长等,“量能” 则是评估自身的实,如优势、局限、资源等,“揣情” 是洞察事物的真实状态,如趋势、矛盾、现状等。
这三者如同司南的指针,能在复杂事务中为行动所定向。、
尚若不知 “材” ,则用人不当;不明 “能” ,则不知可行否;不 “揣情” 则会导致对策偏离实际。而只有三者合用之,才能让行事有章可循而不致迷失。
“度材” 的核心是 “识人”,如同司南辨别方位,它能让人看清到底 “谁可用、谁能用、如何用”。
刘邦知韩信 “善将兵”,故拜其为大将;刘备知诸葛亮 “善谋略”,故托以国事。
反之,若 “度材” 不明,便如赵王用赵括代廉颇,误认纸上谈兵者为将才,终致长平之败。
“度材” 的难点在于看清表象:有人 “言过其实”,有人 “大智若愚”,而 “度才” 之人需如匠人辨木一般,看纹理、试硬度,反复揣摩,方能知其 “材” 之真伪与用途,这是用人成事的基石。
“量能” 的关键是 “知己”,如同借助司南锚定自身的位置,让人明白 “我有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项羽虽有 “力拔山兮气盖世” 之神功可却 “量能” 不足,不知自我,刚愎自用,更是高估了自己 “武力可定天下” 的能力,最终乌江自刎;
而刘邦,知自己 “运筹帷幄不如张良,安抚百姓不如萧何,带兵打仗不如韩信”,故能 “善用其能” 而终得天下。
“量能” 不是妄自菲薄,而是客观认识自我,既知优势,也明短劣势,从而找准自身的定位,避免遇到 “力所不及而强为” 之困境。
“揣情” 的本质是 “明势”,如同司南感知磁场,它让人洞察事物的发展趋势与规律。
诸葛亮 “隆中对” 便揣透了 “曹操不可与争锋,孙权可结为援” 的天下局势之情,商鞅变法也是揣透 “秦民欲强、旧制需破” 的秦国之国情。
而“度材、量能、揣情” 的三者之间灵活运用,便构成行事的 “司南系统”。
“度材” 与 “量能” 可以是 “人” 的维度,“揣情” 可以是 “事” 的维度,如同司南的指针、刻度与底盘,共同作用才能定向。
曹操 “唯才是举”,知自身 “挟天子以令诸侯” 的优势,又揣透 “天下思定” 的民情,故能统一北方;
而袁绍 “外宽内忌”、“志大而智小”,“见贤而不能用”,终被曹操所灭。
二者对比,可见这 “三事” 的协同是成事的关键之一。
然而,度材、量能、揣情并非是一次性就可完成的,三者是需随外界或是事物变化而持续不断的进行调整的。
即使是司南也需定期校准,不然指针便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地壳的不断运动之下,地理磁场的缓慢变化而逐渐变的不再准确。
人的才干会因历练而变,人的能力会因实践而强大,人的想法会因时势而改变。
行事者,需常 “度材” 以更新识人视角,常 “量能” 以校准自我之见,常 “揣情” 以跟进事态变化,方能让这 “司南系统” 始终精确。
如,凡得天下者,皆因其心在于天下,其行在于天下,其思在于天下,由此而为得之天下所谋也。如此,天下何不被其所得乎?
热爱读书写作,愿与你分享经典感悟、文字故事....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钱龙配资-配资炒股配资网站-线上股票配资软件-配资股票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广东股票配资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 下一篇:工程配资当车轮碾过没过半轴的河水